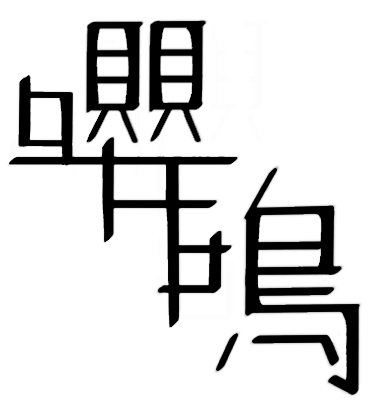亦舒|从亦舒小说看香港都市女性的婚恋困境与出路
- 类别:职场八卦 时间:2023-09-15 浏览: 次
- 文學|藝術|專欄|活動香港都市女性的婚恋困境与出路身为一名“地道”的香港言情女作家,亦舒笔下的多数恋情故事自然都发生在这座繁华都市里。总的来说,亦舒相当关注香港女性的婚恋困境,并在该领域展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10]。台港暨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后女权主

文学|艺术|专栏|活动
听听他的声音并询问他朋友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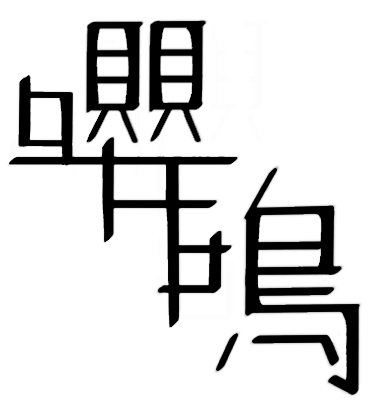
出自亦舒小说
——以《喜宝》和《我的前半生》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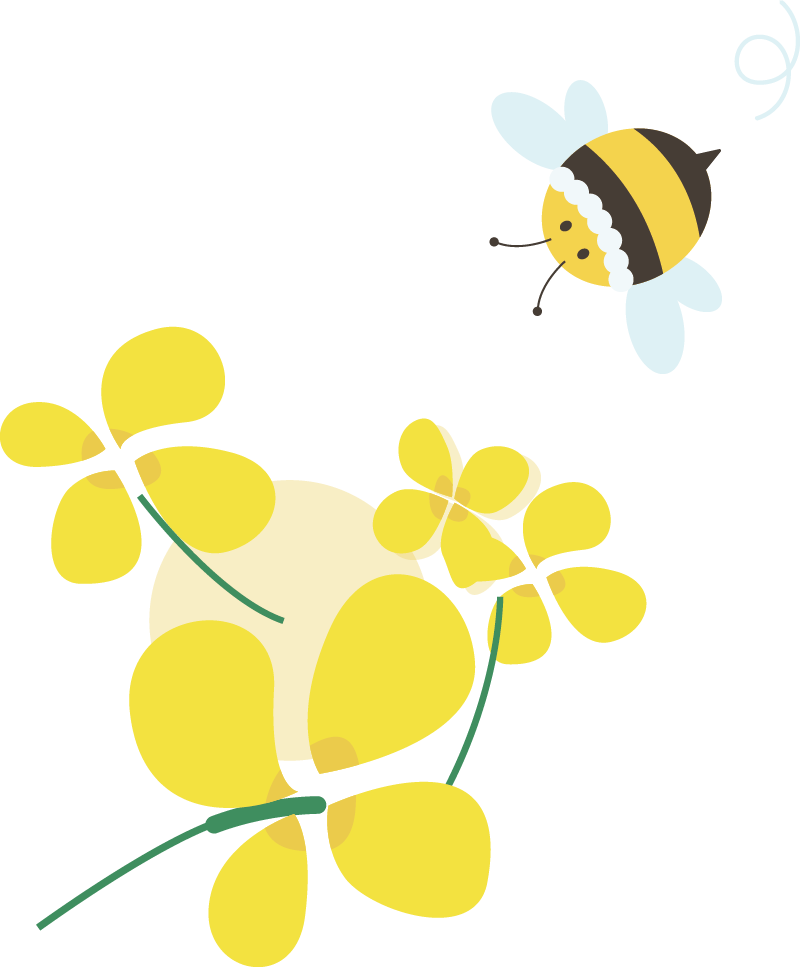
前言
一
作为世界华文文学①作家群中的一员,港台华人女诗人②的特殊性在于她们的离散性和边缘性带来的悬置感,以及对性别关系的包容。 台湾人的思维模式受西方哲学思潮影响,女性诗人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大男子主义理论,以更前卫的态度看待身边的人和事[1]——女性应该有追求除了生活中的情感之外。 ,婚姻家庭不应该成为男人一生的禁锢。 亦舒的奇幻小说就是这样进入公众视野的。
本文将首先阐述亦舒的个人经历和作品风格,然后结合台湾的地域特色分析小说的内容特点和受欢迎的原因。 接下来,作者将结合小说的文字和具体情节,阐释不同男性角色导致悲剧的情感触发因素。 最后探讨亦舒对于台湾都市男性爱情婚姻的理想观,并对全文做一个总结。
————
①广义上是指用汉语写成的、表现华人或其他民族生活的文学作品。 世界华文文学的分类与作者的国籍和种族无关,只要作者是用中文写作的非中国大陆公民即可。
②狭义上,仅指在新加坡、台湾或海外国家用中文描述香港、台湾生活文化的亚洲男性画家; 广义上,指在澳门、台湾或海外用中文描述港台地区生活和文化的女诗人。 没有种族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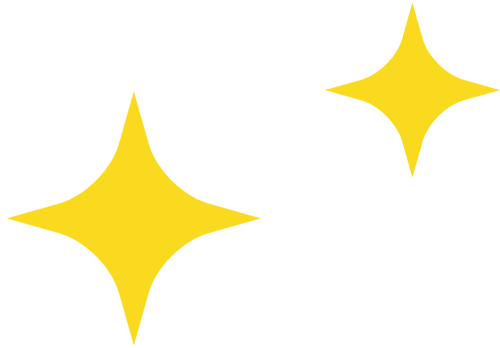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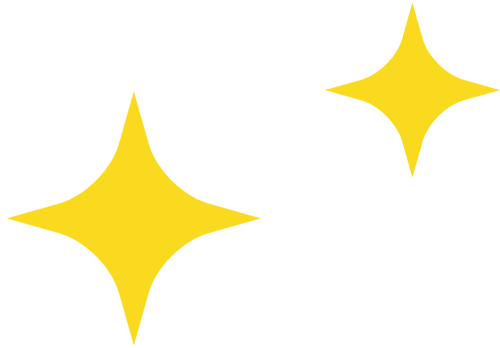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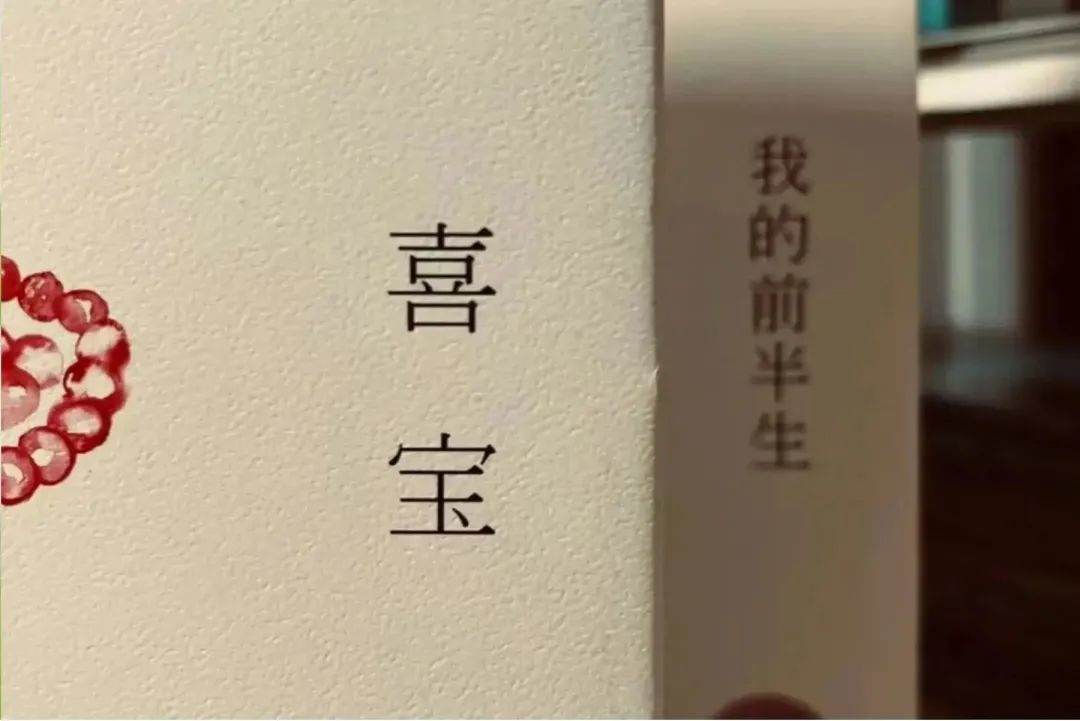

二
亦舒和他的作品
港式爱情故事
亦舒,原名倪亦舒,1946年出生于北京,自幼移居台湾,现移居美国。 她从小学就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至今已出版作品数百部都市职场言情小说有点肉,包括《喜宝》、《我的前半生》、《流金岁月》、《墙舞》等。除了画家之外,亦舒还经历过报社记者、政府新闻官员、酒店经理、公关部长等不同职业。
丰富的生活经历使她能够敏锐地观察到身边人的温暖和温暖,并理性地将生活中不好的一面反映到作品中。 按理来说,出身优越、深受家人宠爱的亦舒,现在不应该发展出如此悲惨尖锐的文笔。 然而爱情路上的艰辛让她无法完全相信感情,甚至决定用作品来揭示这些与感情相伴的东西。 即将到来的痛苦。 年轻时的亦舒也曾梦想过与一个人浪漫一生,但这个幻想很快就因失败的婚姻而破灭。 此后,亦舒站在乌托邦感情的对立面,冷静地揭开一个又一个情感故事的表面,通过主人公所遭受的情感创伤证明“爱情是一场不幸的瘟疫”[2],并提醒公众的糖衣子弹。 保持警惕。 最终亦舒凭借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和切中要害的语言风格赢得了大批读者的喜爱,成为台湾艺坛的代表之一。
作为一位“正宗”的台湾奇幻女诗人,亦舒的爱情故事大多自然发生在这座繁华的都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个东西方文化思想交融之地的经济文化资源突飞猛进,全球化程度直线上升。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智慧和艺术品质,一切都充满了创造力。 国际大都市的独特魅力。 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浪潮的统治下,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逐渐弱化,满足物质需要的欲望被放大到了极点。 情感不再是台湾男女休憩的心灵港湾,而是讨价还价的筹码。 [3]。 浪漫的爱情已经没落,取而代之的是各取所需的快餐式爱情,以及必须被生活压死的“真爱”。 亦舒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告诫读者不要对人际关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生活在情感小说里……简直是惨不忍睹”[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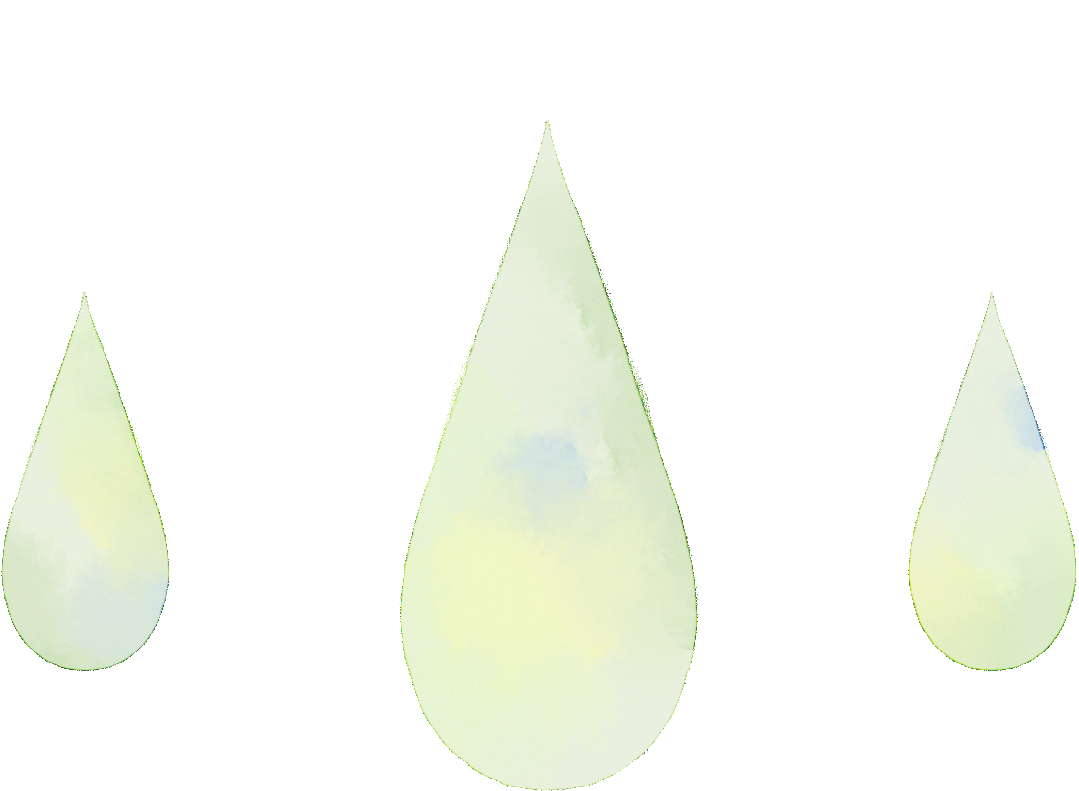
以《喜宝》和《我的前半生》为例,有许从启、方家凯这样门当户对的情侣,有许从敏、赵家明这样的才俊男女,有罗子君、施世平这样稳定的家庭,还有江爱塔美、许存姿等金钱和性交易。 江艾塔梅、冯·埃森贝克·汉斯等秘密交往渠道,个个都被感情伤痕累累,就连他们的暗恋者徐从书也未能幸免。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90年代台湾通俗文学的繁荣和亦舒小说的崛起也与台湾自身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 快节奏的生活、奢侈的社会风气,给大众带来了无形的压力。 人们迫切需要一些休闲方式来麻痹自己躁动的心,而亦舒的文章篇幅合适,可读性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 引起共鸣的台湾奇幻小说满足了时代的需要。 自古以来,爱情题材至今仍为作者和读者所喜爱。 亦舒将这一命题进一步提炼,聚焦台湾各阶层男人在爱情中面临的选择,让不同的读者在故事中看到自己的情感。 这些写照不仅引发思考,更激励读者实现自己的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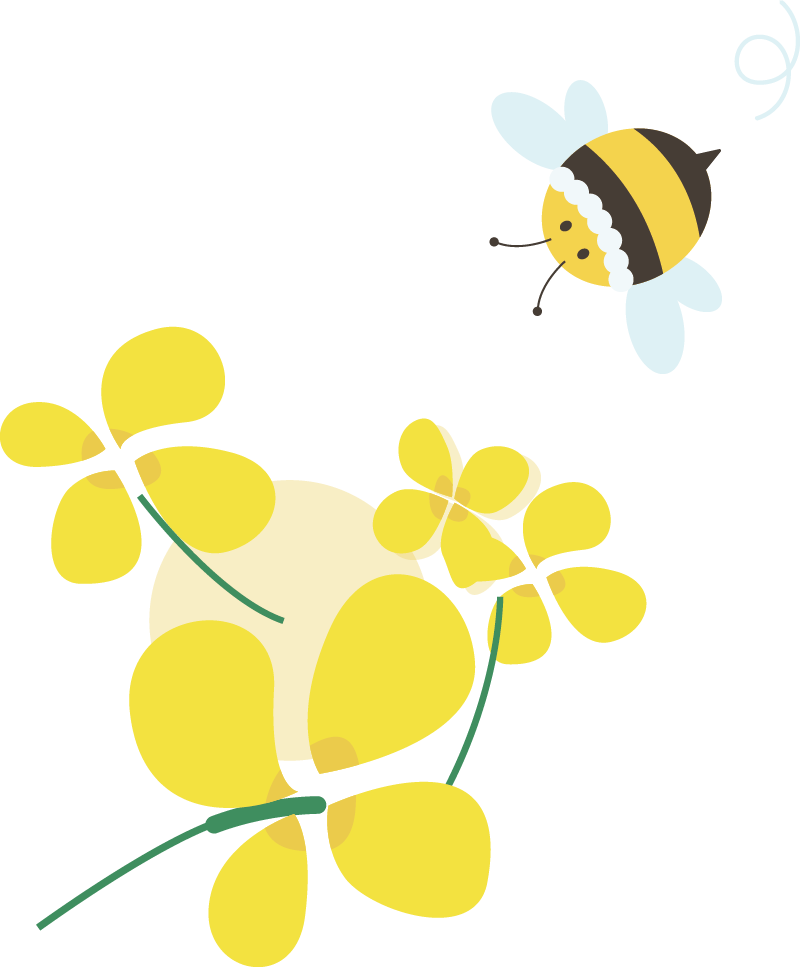
艺术女孩
爱情的曲折
三
由于亦舒的大部分作品都围绕着同一个中心思想,忠实的读者不难发现“亦舒女孩”①有一个共同点:她们普遍追求奢华的生活,表面光鲜亮丽,但他们的内心却充满了莫名的难处。 。 一方面,她们是被现代观念改造的都市新女性; 另一方面,他们是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年轻人[5]。 正因如此,艺树女孩的婚恋观往往是矛盾的。 残酷的现实不断向他们展示自力更生、自力更生的重要性。 生活的坎坷也剥夺了他们“爱”别人的能力和勇气,但他们的内心仍然渴望爱情和家庭。 纵观《喜宝》中的江艾塔美、许聪颖、许从义,以及《我的前半生》中的罗子君、罗子群的婚恋处境,他们对待感情的态度无一不是精神需求和物质欲望的复杂化,爱情与婚姻、传统束缚与现代突破之间的撕裂所诠释与重塑。

说到感情和蛋糕的选择,很多读者都会想到《喜宝》中的姜爱塔美。 似乎有人会说她是“丰收女孩”,鄙视她用身体和爱情换取金钱,但毕竟她只是拜金社会的囚徒。 出身贫寒的江艾塔美,从小就得学会借助性别和美貌来迎合女性,甚至为了得到杂费和生活费而卖身。 如果她是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就好了,但问题是江艾塔美内心深处有爱。 她多次指出自己最渴望的是爱情,其次是金钱,但她没能将两者分开。 聪明的江艾塔美很早就意识到,穷人处于社会食物链的最底层,所以她需要一个能通过物质表达爱的人,或者是一个除了满足她的物质需求之外还能给她一些爱的人。 。 贫困成为制约江艾塔美丽与幸福的最大因素。 社会地位和年龄的巨大差距,意味着她和勖存姿始终无法跨过那道叫做“生意”的坎。 她没有确认自己对勖存子的爱,但她的自尊和自知之明不允许她先动心[3],理智也告诉她,勖存子的“爱”并不纯粹。 这种矛盾的认知让她在压抑的精神世界中迷失了自己。
讽刺的是,江艾塔美曾说过:“我现在什么都有了,我有足够的钱买任何东西,包括我的妻子和母亲。” [6]然而,对于上流社会的人来说,感情也是一种爱。 奢望。 从表面上看,徐家的两个孩子似乎有着让别人羡慕的好姻缘。 幕后,许从民和张家明天天吵架。 徐从启常常想,自己无法生下孩子,所以无法赢回父亲的心。 事实证明,爱情和金钱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穷人计划在富有后寻找真爱,而富人却想体验“有足够的爱和水”的生活。
如果说《喜宝》呈现的是豪门的悲剧,那么《我的前半生》则明确告诉读者,爱情的火花会在柴米油盐的日子里熄灭,一纸婚书对于男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事。 只要你彻底放弃对他人的屈服,就不能保证你能重获生命。 婚后,罗子君是一个聪明勇敢的大学生。 婚前,为了讨好父亲,他变得越来越迷茫,心甘情愿地在两性关系中走向从属地位。 在经历了经济和精神支撑同时崩溃的噩梦后,罗子君被现实催促着要成长,成为一名自给自足的职业女性。 不幸的是,她的职业成就未能弥补她内心的空虚。 罗子君认为,她不再热衷于婚姻,而是希望找到一个值得依赖的优质女人。 在她眼里,婚姻不再只是爱情的延续,而是为了“绑定”一个美好的家而签订的契约。 这样的态度转变,让罗子君在与翟有道离婚后感叹,“至于我的余生……谁会感兴趣呢?每个老太太的生活都几乎一模一样”[7]。
此外,艺树女孩的婚姻困境也是由传统文化观念和周围人的眼光带来的压力造成的。 在性观念相对开放的台湾都市男女眼中,爱情更多的是一种交易或娱乐,因此他们不注重伴侣的独特性,也不坚持要在一起[5]。 然而,这些爱情模式在保守派眼中却变得“不正当”。 以《我的前半生》中坚持与外国人相处的罗子群为例,“不是她喜欢外国人,是中国人不选她,而是一些中国人的眼睛几乎不看她”。 “不要编一首关于她的爱情故事的歌曲。唱这首歌”[7]。其他人的价值观和个人生活方式的不匹配迫使一些男人调整他们的择偶标准,以避免外界的批评。
————
① 指亦舒作品中的重要女性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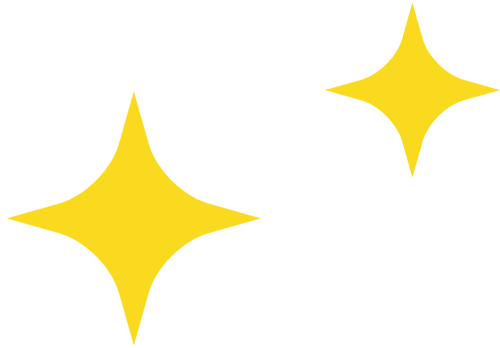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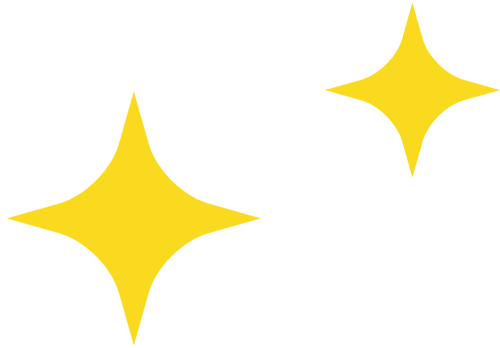


四
台湾都市女性
理想的婚姻观和爱情观
亦舒同情女性所受的压迫,但并不一味地颂扬女性,也不站在女性的立场上指责社会和女性。 相反,大多数艺数女孩都有着明显的缺点,比如沉迷于肉欲的江艾塔美、天真得可怕的徐聪颖、早年缺乏独立意识的罗子君……虽然她们都是受害者在男权社会里,自身的性格缺陷也是造成悲剧的原因之一。 亦舒以平等的眼光看待那些陷入台湾荣光的男女,平等地批评他们,但也真诚地希望他们能够迎来救赎的三天[3]。 为此,亦舒常常在作品中留下几条引人注目的“线索”,试图向读者展示真实生活的都市男人的魅力。 《我的前半生》中都市职场言情小说有点肉,这个“线索”就是唐晶。
作为为数不多的能够过上一帆风顺生活的亦舒女孩之一,唐晶满足了亦舒对于新都市女性的两个愿望,那就是同时实现经济独立和精神独立。 这里所说的精神上的独立包括心理层面上的独立。 唐晶的思想非常前沿。 她相信,失败的婚姻并不会剥夺男人再次追求幸福的权利。 她也承认女性的身体自主权,认为整容是女性让自己美丽的正常方式之一。 此外,唐晶的智慧和能力不仅体现在“职场女强人”的标签上,还体现在她面对生活时的透明和耐心。 当罗子君劝她择偶时不要把目光定得太高时,她把择偶比作订制一块砖石手表,切不可随意凑合。 没过多久,唐晶就找到了与自己相配的人生伴侣。
唐晶的故事直观地向读者反映了亦舒眼中台湾都市女性理想的婚恋观,这也是她自己在电台《再聊歌吧》中提到的:“经济独立、人格独立是关键”女性的独立和成功。” 这是解脱之道,这个时候,你就有资格谈离婚了。 一旦经济独立了,你想嫁给谁就嫁谁。”[8]亦舒深知,对于信奉以家庭为中心观念的东方女性来说,渴望一个温暖的家庭几乎是一种本能,因为她们认为完全脱离情感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9],因此,之前爱情失败的亦舒选择通过作品与自己、与生活和解,并没有彻底抹去“圆满”的可能性。 《我的前半生》结束后,唐晶给罗子君写了一封信,对她说:“何必用‘已婚女人’这个词呢? 爱你的人永远爱你。”[7]。这句话想必不仅是唐晶对罗子君的问候,也是亦舒对自己和依然期待感情的读者的问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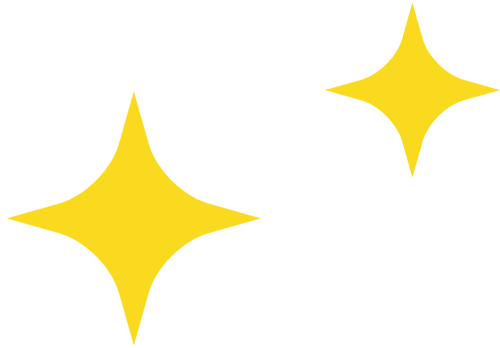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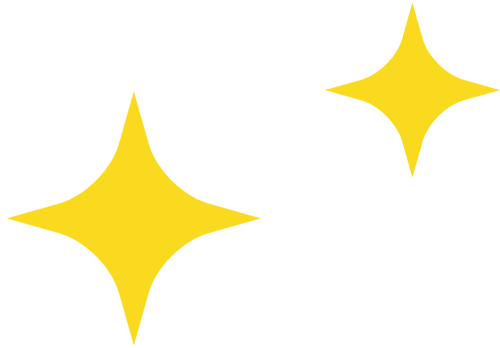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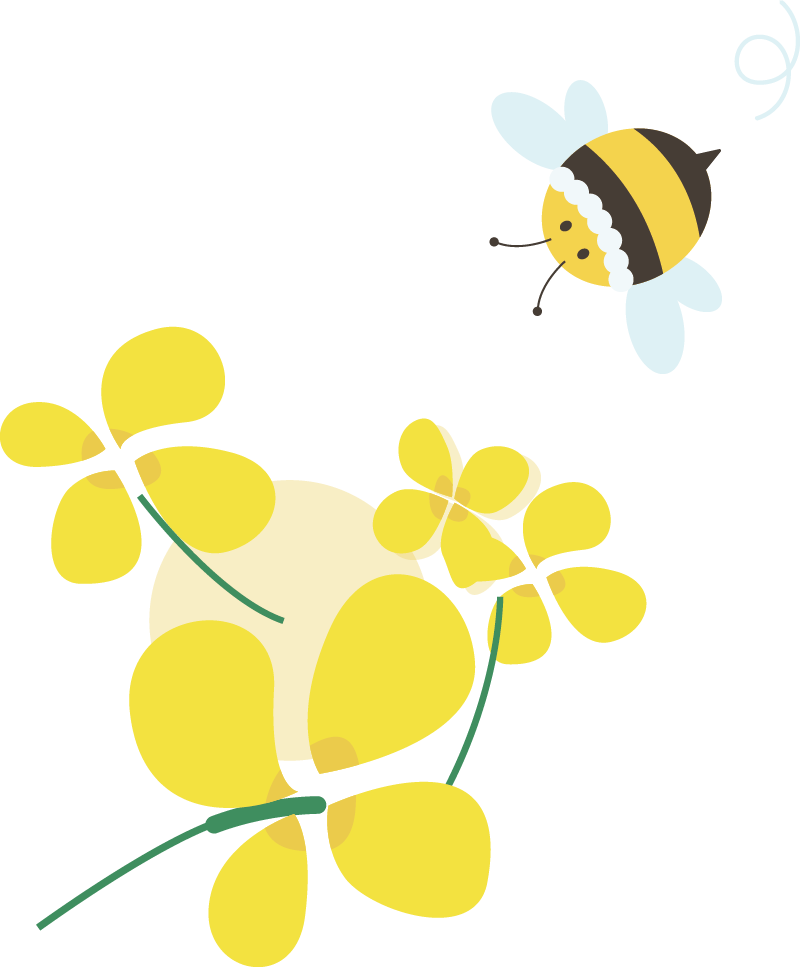
结论
吴
总的来说,亦舒非常关心台湾女性的婚姻困境,并在这一领域诠释了浓厚的人文关怀精神[10]。 她想通过作品向读者传达这样的信息:“属于你的感情可能会在未来三天内如期而至。在此之前,请过好自己的生活,不要恋爱,也不要为了爱而恋爱,为了离婚而离婚。女人要时刻记住自己是属于自己的,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经济上。当她们能决定眼前的“爱”是牢笼还是温暖的港湾时无论最后他们是否选择回到家人身边,他们都会离幸福更近一步。
参考文献(按文中首次出现顺序排列)
[1] 王贻芳. 台湾、香港及海外华人女诗人的后男性主义镜像比较[J]. 云南社会科学,2015(10):60-65。
[2]亦舒. 我的前半生[M]. 长春:南方文艺出版社,1991。
[3]尚继红. 投资时代的情感——亦舒笔下的台湾情感与爱情[J]. 当代艺术界,2004(02):108-109。
[4]亦舒. 曾深爱过[M]. 上海:中国妇女出版社,2012。
[5]刘玲芳. 都市女性的生存[D]. 西安大学,2010。
[6]亦舒. 爱他的美[M]. 北京:海天出版社,1996。
[7]亦舒. 我的前半生[M]. 长春:南方文艺出版社,1991。
[8] 李敏. 论亦舒的女性写作[D]. 山东师范大学,2008。
[9] 田伟利. 亦舒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探析[J]. 山东社会科学,2002(09):79-80。
[10]陈自然. 现代都市女性的生存景观——论亦舒的都市奇幻小说[J]. 名作鉴赏,2010(11):137-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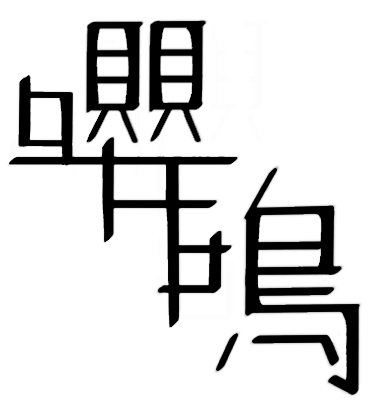

伊芙琳·维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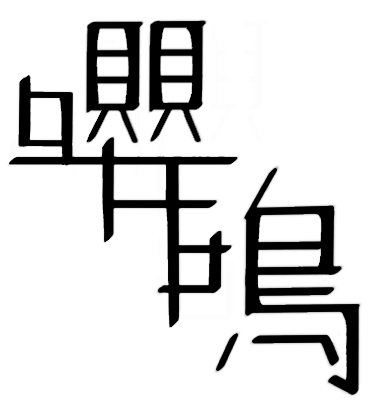
图片|网络
文字| 伊芙琳·维芬
主编|黄嘉文
美术编辑|吴越
这篇文章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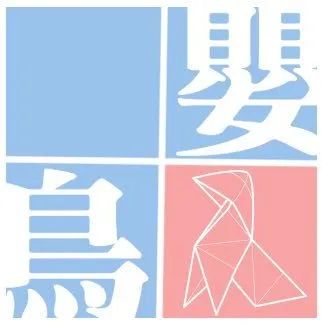
《英明》编辑部版权所有
转载请注明出处